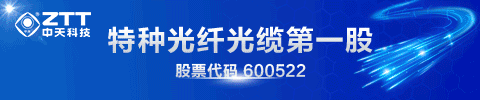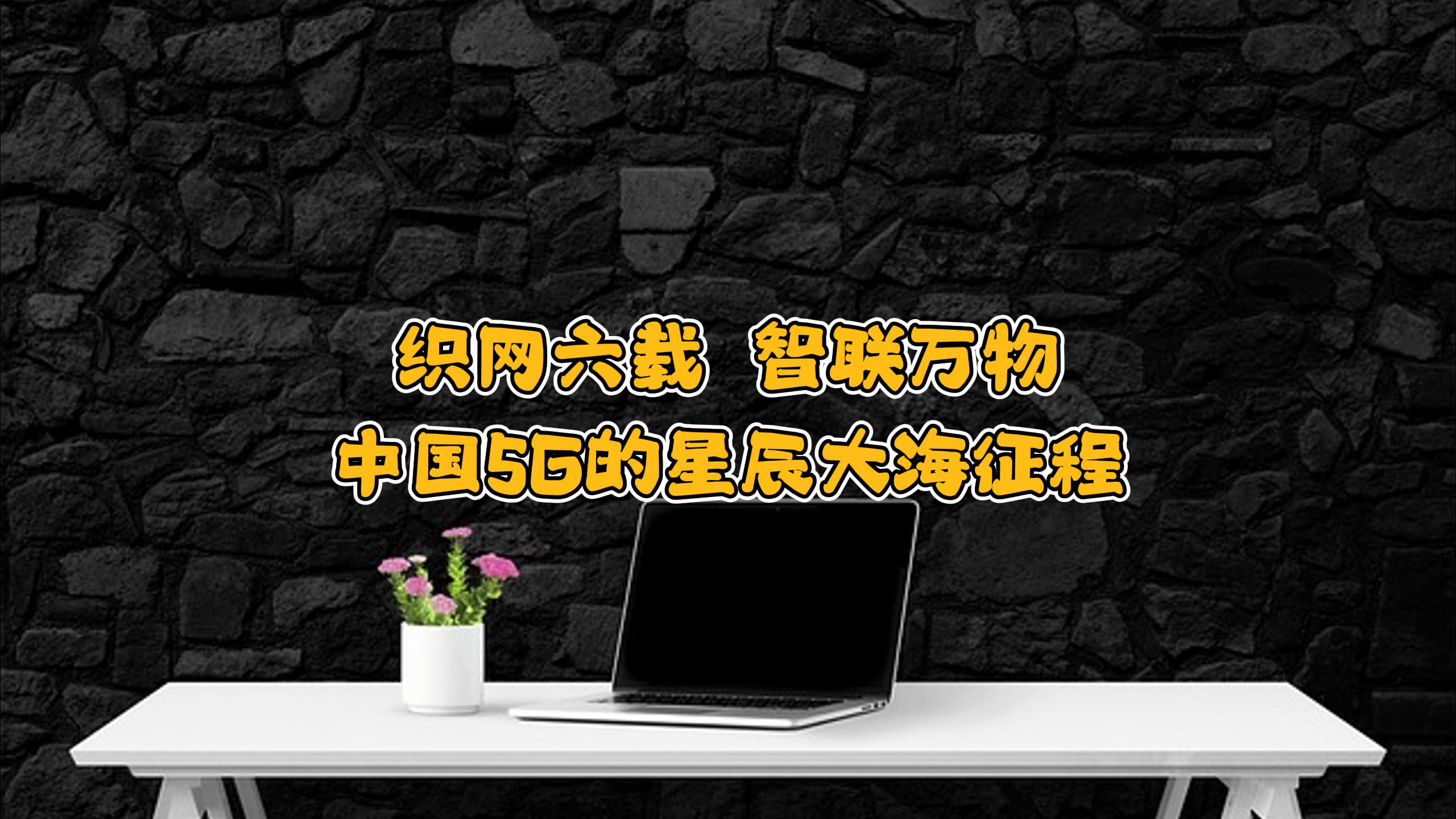飛象網訊(孫迎新/文)如今的就業市場存在一種荒誕的現象:一邊是東莞工廠里的機械臂不知疲倦地旋轉,而曾經流水線上的老師傅卻看著手機里“保安招聘35歲以下”陷入沉思;另一邊是杭州城西的AI實驗室里亮著徹夜的燈,HR對著滿屏“精通NLP算法”的招聘要求直嘆氣,而隔壁咖啡館的服務員正給一群討論“大模型訓練師資格證”的年輕人端咖啡,或許他們正在分享上個月被裁的經歷。

當ChatGPT寫出第一篇通稿時,有人驚嘆“文科生要失業”,可真等某媒體裁掉三分之一編輯后,卻發現剩下的崗位需要“能做數據可視化、會運營短視頻”的多面手,投來的簡歷里卻擠滿了只會寫八股文的畢業生;另一方面,耗費萬億天量資金訓練出來的AI大模型,取代的只是月薪幾千元的“牛馬”工作,甚至更低。
更魔幻的是,蘇州某養老社區掛出“月薪1.2萬招康復護理師”的牌子無人問津,而千里之外的縣城網吧里,一群年輕人正對著“電競陪練月入過萬”的廣告蠢蠢欲動,他們不知道,那些在屏幕前教老人用智能手環的工作,其實比打游戲更需要耐心。
恐慌與迷茫,都指向一個主題: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對就業的影響。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源于當前中國就業市場日益突出的結構性矛盾:“有人沒活干”與“有活沒人干”并存的現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是一位長期研究就業問題的學者,他認為必須直面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對就業結構的深刻沖擊,尤其是其引發的結構性失業風險。
蔡昉認為,從經濟學視角看,技術對就業的影響始終存在“破壞”與“創造”的雙重效應。但今天更需要警惕:這一輪技術革命在速度、廣度和深度上均遠超以往,其對就業的沖擊呈現出全新特征。我們既不能陷入“技術恐慌”的盧德主義,也不能盲目套用“技術終將創造更多就業”的傳統樂觀邏輯,而應立足現實,深入剖析人工智能時代的就業新矛盾。
沖擊特征: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就業格局
技術迭代的“加速度”與“泛在性”是這輪AI變革的主要特征。人工智能與傳統技術的本質區別,在于其自我迭代能力與跨領域賦能特性。
回顧歷史,從1770年“人工智能”概念萌芽到1950年圖靈提出理論,耗時180年;從擊敗國際象棋冠軍(1997年)到戰勝圍棋冠軍(2016年),耗時19年;而從ChatGPT誕生(2022年)到各類大語言模型爆發,僅用1年。這種“指數級加速”背后,是數字技術對試錯成本的革命性降低:如基因編輯技術可通過算法模擬無限次迭代,遠超傳統育種的“年周期”試錯模式。
更關鍵的是,人工智能已從替代體力勞動崗位(如制造業操作工)轉向滲透高智能崗位(如代碼編寫、數據分析)。企業投入巨額資源研發AI的核心目標,是通過減少勞動投入實現勞動生產率躍升。這種“效率優先”的導向,必然對就業市場形成系統性沖擊。
隨之而來的就是,崗位替代與創造的“時間差”與“結構錯配”。傳統經濟學認為“技術破壞就業但終將創造更多就業”,但這一結論忽視了兩個關鍵矛盾:時間與技能。
時間不對稱性:機器替代工人是“瞬間完成”的(如生產線引入機器人),而新崗位創造需經歷“技術擴散-產業重構-技能匹配”的漫長周期。以美國為例,制造業崗位被自動化替代后,低技能勞動者轉向低端服務業用了數十年,而同期被替代者早已退出勞動力市場。
技能鴻溝擴大:新技術應用提高了企業對勞動者的“保留生產率”要求——即雇主僅愿意雇傭具備更高技能、能匹配技術效率的勞動者。這導致被替代者要么因技能不足長期失業,要么被迫接受更低工資(如從制造業轉向餐飲服務業),加劇勞動力市場兩極分化。
因此,蔡昉認為,在此背景下,簡單批判“盧德主義”已無意義。當代勞動經濟學的“搜尋-匹配模型”表明:失業者重新就業需經歷信息搜尋、技能重塑、薪資談判等環節,而AI加速了這一過程的“不平等性”:高技能者可快速轉向新崗位,低技能者則陷入“失業-低薪循環”。
現實印證:中國與全球的就業市場變局
面對中國的典型事實:老齡化、自動化與就業轉型,社會不可避免會產生恐慌,并不由自主地去尋找出路。
同時,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機器人市場(安裝量連續多年全球第一),正經歷著“未富先老”背景下的自動化加速。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自2012年起連續12年負增長,60歲以上人口占比已達20.8%(2023年),迫使企業通過“機器換人”應對勞動力短缺。
這一趨勢在制造業尤為明顯:過去十年,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32%降至27%,就業人數相應減少。退出制造業的勞動力中,少數返鄉從事農業或個體經營,多數流入服務業,但服務業整體勞動生產率(約為制造業的60%)難以支撐薪資水平,導致城市內部收入差距擴大(以泰爾指數衡量,2020年后城市收入差距呈上升趨勢)。
與此同時,非單位就業規模激增:全國非單位就業人數達3.1億,靈活就業人員約2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如網約車司機、快遞員)近1億。這些就業形態雖緩解了崗位短缺壓力,但普遍存在社會保障不足、權益易受侵害等問題。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要參考國際理論與經驗,那映入我們眼簾的會是:老齡化驅動自動化的“阿西莫格魯事實”。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的研究揭示了三個關鍵事實。
老齡化是自動化的新動因:日本、韓國等老齡化嚴重的國家,機器人密度(每萬人安裝量)居全球前列。勞動力短缺推高人力成本,迫使企業采用自動化技術,形成“老齡化→勞動力短缺→機器替代”的因果鏈。
收入差距的雙重擴大:自動化既提高資本收益(如企業利潤),又拉大高技能與低技能勞動者收入差距。美國數據顯示,1980-2020年,前10%高收入群體與后50%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擴大2.3倍,部分源于技術對低技能崗位的替代。
AI應用的“價值選擇”:AI可被引向“提高生產率”或“改善服務體驗”的不同路徑。例如,醫療領域應用AI可選擇“讓醫生看診量翻倍”(創造就業)或“裁員50%”(破壞就業),這取決于技術應用的社會目標與制度約束。
蔡昉認為,“索羅悖論”(計算機技術普及但生產率統計未顯著提升)與“鮑摩爾成本病”(服務業生產率滯后但薪資需與社會平均水平持平)揭示了AI時代的深層矛盾:技術進步可能因應用不均導致“生產率抵消”,而低生產率行業被迫吸納過剩勞動力,形成“就業數量增長但質量下降”的困境。
應對策略:人力資本升級與制度創新
無論科技的問題還是經濟的問題,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問題。因此我們不可避免最終要回到對人力資本的培養:從“知識儲備”到“AI協同能力”。
AI時代的人力資本競爭,已從“人與人的較量”轉向“人與AI的協同”。傳統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力資本標準逐漸失效,核心能力需轉向三大維度:
非認知能力:情商、溝通能力、同理心、創造力等難以被算法編碼的能力。莫拉維克悖論表明,AI擅長邏輯推理(如下棋),但難以完成3歲兒童端水避障等“本能任務”,因其依賴人類數百萬年進化形成的隱性知識。
終身學習能力:技術迭代周期從“十年級”縮短至“年級”,需建立覆蓋“學前教育-職業培訓-老年學習”的全生命周期體系。研究表明,兒童早期發展(0-3歲)的教育投入可使成年后收入提升25%-40%,因該階段奠定非認知能力基礎。
教育資源再配置:在保持公共教育支出占GDP4%的基礎上,向學前教育(如普及三年免費托育)和職業教育傾斜,縮小城鄉數字鴻溝,避免“技術紅利”加劇教育不平等。
當然,能力的培養與資源的配置都離不開制度的保障。因此,對于制度創新,尤其是構建AI時代的就業安全網就成為當務之急。我們將構建以下三方面的制度保障。
普惠型社會保障體系:放棄“識別懶漢”的傳統思維,轉向“兜底+普惠”模式。例如,將靈活就業人員納入失業保險,探索“基本收入保障”試點,確保技術沖擊下的社會底線公平。這符合“瓦格納定律”——隨經濟發展,政府社會支出占比需相應提高。
勞動力市場制度革新:針對新就業形態,建立“平臺責任共擔”機制(如平臺與政府共同承擔勞動者社保繳費),完善集體協商制度,保障零工勞動者定價權。同時,加強勞動立法,遏制“算法歧視”“隱性加班”等新型剝削。
宏觀政策重心轉移:傳統宏觀經濟政策側重解決周期性失業(如疫情沖擊下的臨時裁員),但當前需聚焦結構性失業。通過產業政策引導AI向教育、醫療、養老等“高社會價值領域”應用,例如開發輔助診斷AI以增加基層醫療服務供給,而非替代醫護人員。
未來展望:在技術變革中重構就業倫理
人工智能的終極挑戰,是迫使人類重新思考“工作的意義”。凱恩斯在1930年預言“百年后每周工作15小時”,這在西歐部分國家已接近實現(如德國平均工時34小時/周),但中國仍普遍超過40小時。這一差異背后,是技術紅利分配與社會價值選擇的差異。
馬克思曾設想,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勞動將從“謀生手段”變為“自由自覺的活動”:人們可“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今天,AI正加速這一遠景的可能性:當基礎物質生產由技術承擔,人類將有更多空間追求創造性勞動與自我實現。
蔡昉認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通過制度創新確保技術紅利的社會共享。正如阿西莫格魯所言,“AI的正確道路不是技術決定的,而是社會選擇的結果”。我們需要在效率與公平、技術創新與人文關懷之間找到平衡點,讓人工智能成為擴大就業機會、提升勞動尊嚴的工具,而非加劇分化的推手。
因此積極向前看,人工智能時代的就業變革,既是挑戰更是機遇。個人需以終身學習構建“不可替代的能力壁壘”,國家需以制度創新打造“有溫度的技術社會”。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這場前所未有的技術革命中,守住“人”的價值與尊嚴。

但如果悲觀一點看,AI大潮之后,沙灘上露出的不是通用的救生圈,而是無數個形狀各異的坑:有人捧著舊船票找不到新船,有人盯著新航線卻沒有航海圖。當機械臂開始給機械臂編程,當算法開始優化算法,那些沒來得及重新定義自己的人,正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看著兩邊的路牌寫著“淘汰”與“重構”,手里的簡歷就像一張泛黃的地圖。
是卷贏AI時代,還是被AI大潮卷走,你們自己選。